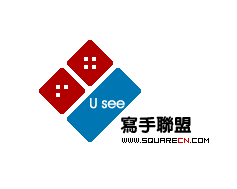故乡琐事
2004-05-12 15:38 | 孤独的心
写手联盟&忘都征文
故乡琐事
大抵是母亲的缘故,至今我还记得老屋前后的那棵梧桐树。
我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些年的七八月份就只能吃小麦。母亲天生手脚灵巧,她设法让我们吃出新的花样。譬如说:我不喜欢吃面糊,母亲就叫我爬上梧桐树,把叶片摘下来,用清水洗干净,放在食盘里。她把办好是面粉,用干净的叶片裹好,放在锅上烙。梧桐叶油量很大,烙热的面粑香气氤氲。这样我能吃饭很多,就避免空肚子去上学。
记忆中,村里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方法。母亲再三叮嘱,不让我把这个“秘密”说出去。我们那里梧桐树很少,如果乡亲们都来摘,树就活不成了。不知道母亲的这个点子是从哪儿弄来的,据说是从祖母那儿传下来的。而祖母又是从哪学来的呢?这似乎没有考证的必要。
结籽的时节,母亲更加忙碌。小孩子们喜欢用石头把梧桐籽打下来玩,母亲一边劝阻一边打虫。梧桐籽熟了,每年收获几百斤,母亲拿去榨油。比如你被竹桩或者其他什么刺伤了,用梧桐油一搽,几天便好。每当乡亲们遇到这种麻烦事,母亲总是很主动地把梧桐油送去,不收人家一文钱。我不明白:为什么她可以拿梧桐油送人,而又不让乡亲们摘一点梧桐叶呢?
我是邻里公认的乖孩子,我没有去问母亲“为什么”。知道许多事不宜问为什么,事实本该如此。问也好,不问也罢。小时候发生在身边的事,随着岁月的流逝,一些早已化作云烟,飘荡或沉淀在记忆的某个角落。关于阿狗,记忆也断断续续。
阿狗是个孤儿,和我一般年纪,很早就死了母亲,父亲是个赌鬼,整日游荡不归,有时酗酒还拿他出气。阿狗也就跑到爷爷奶奶那里住,没事就跑来找我。我们爬梧桐树,或者在树下水洼里打滚,互相往对方脸上抹黄泥,弄到睁不开眼睛为止,然后放声大哭。我记得我们玩得很疯狂,却一点也不开心,彼此之间好象有很重的心事。由于家境十分拮据,外人没有吃到母亲特制的面粑,除了阿狗。母亲对他也不吝啬,每顿总有他的一份。
我问阿狗,你的理想是什么?他低头想了很久,然后猛地抬头,我第一次认真观察他的眼睛:充满野性、稚气、天真。黑亮的眼球,让我想起了湛蓝的大海,抑或无云的晴空。他坚定地告诉我说,别人称我为“独木桥”,没有母亲的孤儿。阿狗愤愤不平。我告诉他,我想走出大山。
我开始茫然,因为阿狗或者我自己。接连我迎来一段失眠历史,想着有关“独木桥”或者孤儿的事情。不去爬树,也不去玩泥巴。有时也想,大山之外到底什么模样。
今天想来,我们都曾有过理想,只是或大或小、或远或近罢了。人与人之间,很不同,很不一样。那时,我们桀骜不逊,口无遮拦。我们想飞翔,不能就此罢休,不能向命运低头。但仅就对命运的理解而言,阿狗和我很不同。他把少年的屈辱、寄人篱下化为仇恨,然后作最大的牺牲,换回所谓的尊严。我说他鸡肚猴肠、睚眦必报。他说我异想天开。
那时,我已经读书。阿狗没有,后来也未曾读过。
十年过去了,阿狗长得和我一样大。跟同村青年一起在外面干了几年苦力,回家娶了个村姑,三年里每年一个孩子。我偶尔回家,看见几个孩子在梧桐树下水洼里打滚,抹黄泥,就象我们当年。我笑着问阿狗,还娶一个吗?他摇摇头。生活真难!她自言自语。当时,他扛着犁铧,萎卷枯黄的头发,满嘴杂乱的胡须,手中夹着一枝老棉烟,燃了一半,眼神却很疲惫。我开始读不懂他,心头有种凉凉的感觉。我却越走越远。从贫瘠的山村到陌生城市读书。我和阿狗已经很少联系了。从家信中得知,农忙秋收阿狗常来我家帮忙。或许,阿狗早把我家当作自家,或者母亲早把阿狗当作自己的儿子。因为阿狗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,而母亲没有一个在家的儿子。
我常觉得,阿狗比我命苦,很小就没有母亲;他母亲又比我母亲命苦,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。
……然而,留下的,就一定快活吗?我不知道。
母亲依然忙碌、辗转奔波,她从没有空闲过。那一年回家,母亲说她大年初五就外出打工。我奇怪地问,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能干啥?她笑着说,趁农忙之前,去离家不远的一个村给人家翻地。母亲依然满脸微笑。我鼻子开始发酸,眼皮在打抖着。幸好,我没有哭。我知道,母亲很好强,她不相信眼泪。
晚上我和母亲一起乘法,我坐在离她很近的地方。她拿着柴杈,把一小堆一小堆松叶推向土灶里。随着一团浓烟滚出来,几条大火舌越过炉门,直朝我们冲来。借助火舌的亮光,我看见母亲眼里闪着泪花。奇怪的是,那是母亲第一次在我面前流露悲伤。母亲经历过很多事:解放前,为避免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土匪,她逃婚;“集体”时期,她背着哥哥姐姐白天黑夜参加劳动抢“公分”;六十年代初闹饥荒她吃过米糠;为了给哥哥读书她卖掉所有的嫁妆;为了挣点家里日常开支的钱,她上山采药,被竹桩刺穿脚……但我从未见母亲流泪。或许,痛苦也需要积累?
推开那扇歪斜的后门走进屋后,我呆呆地看着那棵梧桐树。枯老的树干在风中一颤一颤的,树下一地落叶东奔西窜。人,总有自己想要的幸福,到底是什么。譬如,阿狗和我,还有母亲。
我说,妈,别去了。我不想让母亲为我过度操劳。母亲不语。它还是去了。蹒跚的背影,在我视线里消失……阿狗牵着老黄牛从我身边擦肩而过,满脸的惆怅。我想给他一点微笑,但我没有。
我记起那天黄昏,下了一场大雨,天空格外明亮。那天黄昏,夕阳的余辉也格外霞红。
我想起了阿狗,想起了那棵梧桐树。
-
大抵是母亲的缘故,至今我还记得老屋前后的那棵梧桐树。
我小时候家里很穷,有些年的七八月份就只能吃小麦。母亲天生手脚灵巧,她设法让我们吃出新的花样。譬如说:我不喜欢吃面糊,母亲就叫我爬上梧桐树,把叶片摘下来,用清水洗干净,放在食盘里。她把办好是面粉,用干净的叶片裹好,放在锅上烙。梧桐叶油量很大,烙热的面粑香气氤氲。这样我能吃饭很多,就避免空肚子去上学。
记忆中,村里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方法。母亲再三叮嘱,不让我把这个“秘密”说出去。我们那里梧桐树很少,如果乡亲们都来摘,树就活不成了。不知道母亲的这个点子是从哪儿弄来的,据说是从祖母那儿传下来的。而祖母又是从哪学来的呢?这似乎没有考证的必要。
结籽的时节,母亲更加忙碌。小孩子们喜欢用石头把梧桐籽打下来玩,母亲一边劝阻一边打虫。梧桐籽熟了,每年收获几百斤,母亲拿去榨油。比如你被竹桩或者其他什么刺伤了,用梧桐油一搽,几天便好。每当乡亲们遇到这种麻烦事,母亲总是很主动地把梧桐油送去,不收人家一文钱。我不明白:为什么她可以拿梧桐油送人,而又不让乡亲们摘一点梧桐叶呢?
我是邻里公认的乖孩子,我没有去问母亲“为什么”。知道许多事不宜问为什么,事实本该如此。问也好,不问也罢。小时候发生在身边的事,随着岁月的流逝,一些早已化作云烟,飘荡或沉淀在记忆的某个角落。关于阿狗,记忆也断断续续。
阿狗是个孤儿,和我一般年纪,很早就死了母亲,父亲是个赌鬼,整日游荡不归,有时酗酒还拿他出气。阿狗也就跑到爷爷奶奶那里住,没事就跑来找我。我们爬梧桐树,或者在树下水洼里打滚,互相往对方脸上抹黄泥,弄到睁不开眼睛为止,然后放声大哭。我记得我们玩得很疯狂,却一点也不开心,彼此之间好象有很重的心事。由于家境十分拮据,外人没有吃到母亲特制的面粑,除了阿狗。母亲对他也不吝啬,每顿总有他的一份。
我问阿狗,你的理想是什么?他低头想了很久,然后猛地抬头,我第一次认真观察他的眼睛:充满野性、稚气、天真。黑亮的眼球,让我想起了湛蓝的大海,抑或无云的晴空。他坚定地告诉我说,别人称我为“独木桥”,没有母亲的孤儿。阿狗愤愤不平。我告诉他,我想走出大山。
我开始茫然,因为阿狗或者我自己。接连我迎来一段失眠历史,想着有关“独木桥”或者孤儿的事情。不去爬树,也不去玩泥巴。有时也想,大山之外到底什么模样。
今天想来,我们都曾有过理想,只是或大或小、或远或近罢了。人与人之间,很不同,很不一样。那时,我们桀骜不逊,口无遮拦。我们想飞翔,不能就此罢休,不能向命运低头。但仅就对命运的理解而言,阿狗和我很不同。他把少年的屈辱、寄人篱下化为仇恨,然后作最大的牺牲,换回所谓的尊严。我说他鸡肚猴肠、睚眦必报。他说我异想天开。
那时,我已经读书。阿狗没有,后来也未曾读过。
十年过去了,阿狗长得和我一样大。跟同村青年一起在外面干了几年苦力,回家娶了个村姑,三年里每年一个孩子。我偶尔回家,看见几个孩子在梧桐树下水洼里打滚,抹黄泥,就象我们当年。我笑着问阿狗,还娶一个吗?他摇摇头。生活真难!她自言自语。当时,他扛着犁铧,萎卷枯黄的头发,满嘴杂乱的胡须,手中夹着一枝老棉烟,燃了一半,眼神却很疲惫。我开始读不懂他,心头有种凉凉的感觉。我却越走越远。从贫瘠的山村到陌生城市读书。我和阿狗已经很少联系了。从家信中得知,农忙秋收阿狗常来我家帮忙。或许,阿狗早把我家当作自家,或者母亲早把阿狗当作自己的儿子。因为阿狗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,而母亲没有一个在家的儿子。
我常觉得,阿狗比我命苦,很小就没有母亲;他母亲又比我母亲命苦,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。
……然而,留下的,就一定快活吗?我不知道。
母亲依然忙碌、辗转奔波,她从没有空闲过。那一年回家,母亲说她大年初五就外出打工。我奇怪地问,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能干啥?她笑着说,趁农忙之前,去离家不远的一个村给人家翻地。母亲依然满脸微笑。我鼻子开始发酸,眼皮在打抖着。幸好,我没有哭。我知道,母亲很好强,她不相信眼泪。
晚上我和母亲一起乘法,我坐在离她很近的地方。她拿着柴杈,把一小堆一小堆松叶推向土灶里。随着一团浓烟滚出来,几条大火舌越过炉门,直朝我们冲来。借助火舌的亮光,我看见母亲眼里闪着泪花。奇怪的是,那是母亲第一次在我面前流露悲伤。母亲经历过很多事:解放前,为避免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土匪,她逃婚;“集体”时期,她背着哥哥姐姐白天黑夜参加劳动抢“公分”;六十年代初闹饥荒她吃过米糠;为了给哥哥读书她卖掉所有的嫁妆;为了挣点家里日常开支的钱,她上山采药,被竹桩刺穿脚……但我从未见母亲流泪。或许,痛苦也需要积累?
推开那扇歪斜的后门走进屋后,我呆呆地看着那棵梧桐树。枯老的树干在风中一颤一颤的,树下一地落叶东奔西窜。人,总有自己想要的幸福,到底是什么。譬如,阿狗和我,还有母亲。
我说,妈,别去了。我不想让母亲为我过度操劳。母亲不语。它还是去了。蹒跚的背影,在我视线里消失……阿狗牵着老黄牛从我身边擦肩而过,满脸的惆怅。我想给他一点微笑,但我没有。
我记起那天黄昏,下了一场大雨,天空格外明亮。那天黄昏,夕阳的余辉也格外霞红。
我想起了阿狗,想起了那棵梧桐树。
-
宠 辱 不 惊 看 花 开 花 落
去 留 随 意 任 云 卷 云 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