钗头凤…【国魂】
2008-12-22 21:48 | 林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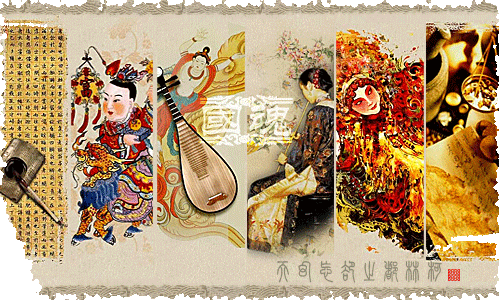
| | 钗头凤…【国魂】
§ 难!难!难! 远远地,国帮就在门口探头望见义明,想是早已等候了多时,忙不迭地迎上来叫“少爷”,帮忙接了行李,遂一同寒暄着进了宅子。 早已有人进去通报,刚穿过前院,三姐亚兰便欢喜着赶出来,上前拉了手拍到,叫说“四弟呀你好歹可到了,不知盼得我们好心焦”,义明只是笑,正要开口,其他人也都随着父亲母亲出来。众人见到底好好的回来了,方安了心。 又是七嘴八舌了一阵,这才入客厅落座上茶。义明大约说了说今次出去的经过,收帐不顺利,大多户人家,也是亏空。父亲叹气说是原想借着机会,让出去闯闯,怎逢着如今米价抬得天高……话到此处也就停住,不由地愁上眉梢。母亲本想就着埋怨让孩子独自出去,奈何丈夫正是心烦之际,不便多言,只回头嘱咐义明以后不许这么耽搁,现今不太平,家里上上下下担心得紧,方才就派人去打探了好几次。义明自是点头应允,众人又闲谈几句,母亲思量着他旅途劳累,也不让久留,叫赶紧下去,好生休息。 答应着起身,义明这才忆起什么,转头问身边三姐,说怎不见了大哥。亚兰闻言急抬手刚想止住,奈何话已被父亲听了去,不知怎地顿时就变了脸色,拍桌起身咆哮道“别提那败家子!” 众人一惊,霎那哑了一屋子人,义明更是回不过神。三姐转头埋怨着叫了一声“爸爸”,旁边母亲赶紧打圆场,“哎呀呀”地站起身过去拉丈夫坐下,劝慰言道“怎地发起老四的脾气来了”,回身使了眼色,亚兰灵醒,一看会意,招呼着众人退了出去,只二姐玉清刚刚随着走到门口,独独被父亲抬头叫住,留下来说话。 亚兰连同五妹淑珍、六妹碧清随着义明同进了里院,到了廊子上,看四下无人,才说起大哥的事来。 “不过是结婚的事情,大哥自是心有所属的,这女子,想来四弟你也是认识的…”不等三姐说完,义明会意,笑着抬手冲西边指了一指,三姐点点头道,“正是她…” 西边姓方的大户人家,长女是大哥义沛的青梅竹马。两家人一直相交不错,义明等兄弟姐妹和那边同辈自小一起长大,大哥两人的事情他们自然是知道的,相好本是情理之中,也应算得门当户对,出了甚岔子不成? 三姐听义明这么一说,不由地撇嘴苦笑,摊手在掌上用指写了一撇,又画了一捺,言道:“四弟你信么,八字不合…” 义明一听,不由得笑,说三姐你唬我不成,这八字不合还能从小玩在一处、到如今打都打不散?六妹一听嚷嚷四哥叫说真的真的,还欲发话,被亚兰低喝一声“碧清”,往西房方向使了眼色,六妹收了声扭头一瞅,知是大哥的住处,被听了去总是不好,缩首回来,吐了吐舌头,忙捂了嘴巴。 三姐转头满脸无奈地摇摇头,压低声音,方才说了来龙去脉。 原是此前来了別家的媒婆说亲,大哥本以为是方家来了人,后来才知不是,又于暗处听见父亲言谈之间,似有允诺之意,一时惊得慌了神,也不知缓缓,竟闯将进去,顶撞起父亲来。偏偏遇着来的媒婆,也不明是收了提亲那家子多少,见有人冲进来拆台,赶紧旁边迎合着,胡说瞎扯的,什么方家八字不合克夫败家之类。大哥一时恼,差点没打了那婆子,羞得她回去这么添油加醋一说,也就吹了。吹就吹便也罢了,事儿传开来,方家自然是知道了,原本这祸端是提亲那家子惹的,过去了也就好了,哪知父亲气上心来,还就是不准大哥和方家小姐再来往。 末了三姐叹口气,说现如今不单大哥和方小姐,就连这些个弟弟妹妹,和着丫头下人,都再无走动。义明一愣,问说方家怎也就如此? 三姐低声嗨地言道:“你还想不通怎的?方小姐别人家那也是大户,女儿家家的,先被人无端端地抹黑一通,而后还要看你等脸色,那才是做了贱了,怎会甘休?” 亚兰皱眉压住心火,长舒口气:“也怪那大哥和爸爸两人,真个犯了魔一般,爸爸平日里脾气燥,那也都罢了,连一向稳妥的大哥这会都冲得要紧,钻了死理谁都不认,四弟你有见过大哥发脾气发到这份上么?还要打媒婆了……” 碧清闻言,似又忆起当日那婆子跟只老母鸡在屋里瞎撞情景,哧哧想笑,好歹才收住。义明楞了半晌,只摇了摇头,却也着实想不明白,几人竟各想了事,都无有话说。末了还是亚兰回过神气,对义明言道她和姐妹们都是女儿家,父亲也正在气头上,外事又不断,不好多参言,拿着没法,就等四弟你回来,幸许可以劝劝。 义明一时间也没个主意。三姐见他发愁,忙安抚说也不急在这一时,义明点头答应着,说只有等着父亲这口气消了,瞧着机会劝劝,兴许便会好了。三姐点头说是,便让义明休息去,几人就此散去不提。 § 病魂常似秋千索 义明收拾停当,稍稍歇息,略一思量,终究是放不下,想先会会大哥,遂到了西房,抬手犹豫一时,这才敲了房门。里边应了,义沛开门见是四弟,先是一愣,然后笑着拍了脑门道:“我总叫他们不要烦我,结果连你今天要回来都忘个干净。” 义明也笑着埋怨:“是了,大哥你这闭关闭得连兄弟我回来都忘记,怕是走火入魔、真个闭了心窍了哟。” 义沛笑着摇头,狠狠拍了老弟一下,让进门去:“不错呀,你这小子出去这么些日子,晒得黑了,嘴也是利索了许多,早晚也得和亚兰有一拼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 “我怎比得上三姐,大哥不知道么,家中上下早早有云,外事不决,可问大哥,内事不决嘛…那还就得问三姐了,于是乎……”义明也不准备多费口舌,进了门转身收住笑认真道,“…三姐还就真个说了些家事……大哥你入魔的事情,委实,也是有的…” 义沛一听一怔,抬手临空点着义明鼻头,复又笑道:“我就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店……”义沛知道四弟若是回来,早晚也得过问此事,就不岔开话,遂进屋搬了凳子出来叫他坐,自己也靠着书桌坐定,叹了气,想了一想,这才开口,说是现今似乎已是到了死胡同,走不出来了,父亲不得妥协…… 话到这儿便又愣住,义明一向知道大哥,见如此料想义沛定然是心意尚未决断,于是问说大哥你可有想过顺父亲他老人家的意思。 “顺着他老人家么?”义沛一听,抬头望着义明,略想了想,开口言道,“先前我想读文学,他想我帮着打点生意,以后好接了他的过去,要我学经济,我就顺了。现在这一辈子的事,也要我顺着么?”义明尚未答话,义沛又言道:“我不想突然地就…面前多个别家的陌生女子,应付不来……和她……打早就好,这你们也是知道的……我万不能断了这份情意。父亲那儿,我虽然不愿弄到这般地步,竭尽所能想要他回心转意,不过……怕是不能的了。” 义沛原想大哥一向做事稳重,怕这次只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,好生劝劝,想通了,一家人总不能僵到怎样,哪知自己疏忽了一点。 情之一字。 义明一时无言以对,惊觉自己竟无有话说,自己做兄弟的,按说是了解大哥的,却说出方才的那些混帐话来,不觉很是惭愧。 又想到若不是义沛稳重,这事情在自己回来之前,早已经折腾完,鱼死网破收拾了。现在才到底弄明白三姐说的难办——他们这些个弟弟妹妹的,是看着大哥与方大小姐好起来的,自是希望他二人白头偕老,却也不愿因为这事情惹得父亲和大哥倒就此翻了脸,这手心手背都是肉,还真乱了方寸,没个定论。 义沛也知弟弟妹妹关心,但终究是自己的事情,不愿拖累他们许多。义明由来温和纯善,比不得亚兰灵醒嘴巧,也不似碧清直性子,见着义明默然不语,便笑笑,拍拍他的肩膀,说自己并无大碍,叫他回去休息。义明要想说什么,却只是不能言语,唯有道别起身。 走至门口,听义沛轻声唤四弟,转身看时,大哥立在桌旁,手里握着一本书,木木地卷将起来,抬头愣愣地盯着窗外,轻轻言道:“……等你们遇着了倾心的人,那时候自然也就明白……” 窗外茶花,朵朵含苞,正待开放…… § 瞒!瞒!瞒! 义明别过大哥出来,只觉心里堵得慌,没个主意,思量难道自己真个身体劳累,憋不出个主意?欲回房先歇歇,哪知脑子里纷纷乱,挪着步,竟反了方向,到了东园前的廊子上,抬头间,却见一人急匆匆从前厅方向跑进东园月亮门。义明见身影熟悉,顿时反应过来,赶上去待看个究竟,门里却闪出亚兰,这当儿正回身抬手要喊什么,复又止住。义明轻轻唤她一声,亚兰听得回头,义明指指她身后,还未问话,亚兰又回首望了两望,转过头来先叹了气,摇摇头。 义明见三姐默然,便叫她一声,又指指方才那人去的方向,回手往自己眼角竖着比划了两下,亚兰点点头,莫奈何地张口言道:“我说四弟呐,今儿个都怎么了,打头的两个人,怎就这么要人操心啊……” 跑过来照应着前面的丫头,亚兰叫住问话,答曰也不知道怎的,远远只听得屋里闹了几句,就见二小姐抢了门哭着跑进来了。怕有个闪失,跟过来照顾着。 亚兰问老爷安好否,答曰尚好,就也不知怎得气得不行,国帮照顾着已回房了。亚兰点头又问来的客人什么的,说到此丫头更是满脸疑惑委屈,说还在门口就听国帮说了,似乎刚才来的客人已被老爷撵出去了,还正发愣就见着二小姐冲出屋了,与她撞个满怀,端的点心茶水洒了,还烫了手。亚兰见她右手通红,略想了想,说这会儿二小姐想必正烦,不便打扰,待会由她亲自去劝慰,又叫先去治治烫伤,安抚两句,招呼着让其下去了。 义明一直在旁听着,待到四下无人,这才张嘴叫亚兰:“三姐,难不成那客人是……” 亚兰又是只点头不答话,好一会儿才说起刚刚的情形来。 亚兰方才在廊子上碰着那丫头端了点心正过,以为是给义明送去,便远远地唤住,说义明这时候正歇着,待会再送去。答话说不是给四少爷的,是之前就来了客人。亚兰问是什么客人,答曰是个教书的先生。亚兰本是随口问问,这一听不要紧,顿时着了慌,收了脚步又细细问了,心想不好,赶紧去寻二姐,到了房门口却没见人,一问反说是到前面迎四少爷还没回来。 “我这才回神,方想起爸爸留了二姐有话讲,怕是知道了,忙赶过来。才走到这儿,玉清就擦着身子奔过去,掩着面,定是哭了。我原本要喊,想她现在难过得紧,你看她平日的脾性,这会儿任谁都不会理的,也就没喊,可巧你也在了……” 亚兰说完,仍旧叹气,义明正想说话,亚兰复又想起不能放着玉清不管,“哎呀呀”地跺脚,赶紧拉了义明,往玉清房间急急奔过去,口里只是嘀咕,说是“早不来晚不来的”,义明知道是说那先生,转念一想父亲总是要知道的,早晚的事,只是不巧撞这个节骨眼上了,没奈何。 敲了玉清房门,只闻里面隐隐哭声,也不答话,要推门,哪里推得开,两人正要喊人,听得玉清在里面好歹止了哭声,凄凄哀哀叫亚兰,说让他们莫急,只想自个儿静静。说完又是抽泣不止。 亚兰又气又急,一时也忘了压火,只管埋怨着道“你这学生当的”,义明忙拉她,摇头示意止住,招呼赶来的丫头让好生伺候着,抬头临空叫二姐莫气坏身子,父亲那儿他们去说说,言罢拉了亚兰便走,背后屋里玉清听得,突然间不知是哭是笑,叫说:“没用!没用!!义沛般配都难成,我能如何……门不当户不对,我能如何,这门不当户不对,我能如何……” 亚兰与义明又往父亲那边赶,义明路上问亚兰,先生怎个现在寻来了。亚兰急急道,怕是之前玉清给他说了,自个儿要找着空儿给父亲讲……义沛的事情,她好些天没出去,先生那儿,许是以为父亲不答应,还不让玉清出门,一急,便就来了。末了仍摇头没奈何地叹道“都赶巧撞一块儿了”…… 母亲领众人在房门口围着,见他们来了,未等近前,便由丫头搀着迎上来,抬手示意他们小声,亚兰也就没说话,赶紧帮忙扶着,轻声问道爸爸怎样。旁边丫头答曰无碍,现在已经睡了。 母亲在旁哀愁满脸,拉着亚兰怨道:“他这脾气,较起真儿来,谁都不认,只以为老了会收收了,哪知越发没个头,看吧,现在又是谁都不让见了……”转头又找人问玉清,亚兰接口道他俩正从那儿来的,母亲闻言忙问二丫头怎样,亚兰说了,母亲只是皱眉,半晌开口问,说二丫头的事,你们几个大的是知道的么。 亚兰一听望望义明,知道无甚好瞒,只得点头,母亲哎呀叹道:“怎不早给我说……” 亚兰赶忙抚着母亲背心顺气,口里直说别怄:“我看这事儿,早说也没什么差处,父亲那,定然是过不了关的……” 母亲抬手让众人散去了,要往玉清房去,听亚兰劝说现在等玉清静静,也才听得进去话,略一思量,也觉得是个理,便允了。旁边义明接手过来,和亚兰一边一个搀着,后边跟着五妹六妹,都没心思回房了,干脆陪母亲回前厅歇息。 路上母亲只是叹,言道:“二丫头从来太闷,什么事都放在心里,也是自小病害的,寻思着出去读读书,多见点世面,些许会好……哪知今天如此……”又指着亚兰道,“以前我只不放心她身子,读书伤神……她要是有三丫头你一半脾气,有什么说出来商商量量的,我也就不担心了……”亚兰只管劝慰…… 众人回前厅落座说话,自是讲义沛玉清的事,不提。 § 世情薄 人情恶 说话间不觉已到晚饭时候,本该给义明接风洗尘,怎奈如今这般模样,一桌子坐定,独独缺了三个,有人去叫,也答不来,母亲自是十分烦闷,闻言丢了碗筷满脸气恼。 亚兰见状,给义明使了眼色,起身过去叫了妈妈,说刚才义明去叫爸爸,不是赌气不来,只是刚才急一场,头有点昏沉罢了,歇歇就好,没甚大碍。义明点头称是,母亲只是不语。 “妈妈你还不知道爸爸脾气么,心里是惦记我们的,不然也不会处处要为我们打算,就是天生性子急,气一过也知道自己没收住,有点过火……”亚兰见母亲稍稍宽颜,又抚着母亲肩膀,“过两天是您的生日寿辰,我们这还准备着呢……” 母亲一听只是撅嘴,一扭肩膀偏头埋怨道:“寿辰?莫让这一老两小收了我的命便是好事,还管得什么瘦辰肥辰……” 亚兰等人见母亲赌气如同孩童,不禁笑了,义明起身笑道:“妈妈说的什么话,为给您祝寿,我可是赶着回来的,还指望仗着寿星的威风,拉他们出来好好坐着,说说话,一家人,哪里有隔着门赌气的……” “可不是么。”亚兰点头道,“妈妈前些时候发善心留着的戏班子,如今还在后院住着,昨儿个还找到我,说当初逢着太太慈悲,收留他们,无以为报。听说马上就到你生日了,知道你喜欢看戏,特意备了两出,那天要演给您看呢……” 母亲一听,隐隐含笑,抬手点亚兰鼻头:“死丫头嘴巧,外边兵荒马乱,他们当初逃难来这,不就是被你看到,为等我生日逗我开心,才留住的么?” 亚兰一听哎呀道:“我有心留,这许是不许,还不是您答应才算数么……” 母亲微微笑,抚着怀里碧清脸蛋,柔声说看这般被人说三下九流的,其中孩子还不是和你六妹一样大,这年头饱饭都难得一碗,能救人自是好事。 转头又道:“我知道你为我高兴,只是眼光浅了些,外边局势如此,我们也不铺张,往年那些个外边的人,这次不请,请也难找到人,就依你说的,演两出,团聚团聚,我们自家乐乐就好,去个晦气。最好你大哥和你二姐的事,能就着当儿,好生说说……” 亚兰一听自是连连答应,母亲这才抬头让人叫厨房挑了几样菜,给父亲和义沛玉清送过去,又差人去看看戏班子那边,有甚需要没有。六妹碧清在母亲怀里,此刻闻听,撒娇叫道妈妈我要看孙悟空。 母亲这时候才转忧为喜,咯吱着碧清在自己怀里乱扭,笑道你这小丫头不比那猴头省心,一家人这才笑开,亚兰义明对望一眼,好歹长舒了口气。 § 泪痕红浥鲛绡透 饭毕,亚兰义明先母亲一步到了父亲房里,如此这般,只管说借着母亲生日机会,要劝大哥二姐。现在眼见没有其他法子,父亲自然是喜欢的,也就应了下来。 其后义明亚兰分头到大哥二姐房里,也只说母亲生日,等到时候父亲高兴了,再说说,许有可能挽回,两人琢磨着好歹母亲生日,总不能一直僵下去,最后便也应了。 只是玉清从来优柔内敛,凭亚兰讲得口干舌燥,说什么都拿不定主意,思量半天,闷闷总是不应。亚兰正着急的功夫,义明这边已和大哥说好出来,到了廊子上,本是约好的亚兰,却不见人,怕二姐那边劝不好,正要去瞧瞧,却不知怎的住了脚步,转身走后院来。 …… 义明竖耳细听,似确有女子声音,词曰“十七岁浮生梦多少孽冤,可怜我没娘儿寄人篱畔”,辨的是《黛玉焚稿》一出,再一细听,却没了,转角儿又听得念白,道的是“我是睹物思人”,心想这个出自何处,心中疑惑,加快脚步到了后院偏房,暗处却又停住。 一女子模样的人站在门前院坝里,身着白花褶子,绣边白裙,其余没甚行头,发也散着,侧面看过去,未施粉黛,清唱而已,手里却拿一手帕,走的戏曲身段,口里正唱到“见一幅罗帕在埃尘”,便住了,只是掉了魂儿一般,两手捏着手帕,只管念叨此句:“见一幅罗帕在埃尘……在埃尘……” 义明一听,忆起此前一句“睹物思人”的,知道唱的《钗头凤》。只是刚才那句“见一幅罗帕在埃尘”,却应是扮陆游的小生所唱才是。此一阙,哀婉缠绵,言言血泪,此时听来更甚,心中难免不快,张嘴要说话,听得有人低声喝曰“快些住了”,还未看时,身后已急急走出亚兰来。 那院里的女子本正入了心境,魂牵梦绕的,这一下惊得不轻,低声啊了一下,转身过来,唬得说不了话,略一定神,见是三小姐过来,知自己唱的那些过于凄哀,惹人厌了,忙不迭用帕擦了擦眼角,诚惶诚恐迎上来赔礼,只是低头,细声细气叫了声三小姐,就再不言语,只等着挨训。 义明细一打量,竟是个年轻姑娘,不过十六七岁光景,模样俊俏,身形也姣好,怎奈眉宇之间,恰有不解哀愁,双眼红红的,想是方才哭了。 亚兰正要说话,旁边跟进来一中年汉子,忙叫三小姐,只管埋头赔罪。亚兰也没发火,问那女子,唱的可是《钗头凤》,女子只是点头。亚兰略有所思,看着她,轻声曰太过哀怨,女子咬着嘴唇,手指头搓着手帕,也不再应。 旁边汉子忙说三小姐莫怪:“……这孩子姓陆,虚岁未满十七,孤苦一人,本来有个丈夫,说来还是打小结的娃娃亲,女孩儿本来不依,结果两家常常走动,竟还好上了,按说是件顶好的事儿,哪知打仗,都给毁了……我原本是她们家邻居,看着两个成了孤儿,好心收他们随班子一起,练出个两段来,讨口饭吃……”话到此处,汉子叹口气,“逃过来的路上,那孩子给军阀开枪打死了……” 女孩儿早已抽泣不止,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,汉子侧头看看女孩儿手里的帕子,回首又对亚兰道:“……我们要给太太排戏,怕吵了人,都出去到后山上练的……你看我忘了东西回来取,怎么就遇着……三小姐莫怪,这孩子从那之后,都只管念叨些凄凄哀哀的词儿,我一思量,这哪儿能生日时候唱呢,就没让她上,留她看屋,哪知道吵了三小姐……” 亚兰早红了眼睛,长出口气,抬手止住汉子:“……我也不是责怪什么,张大哥也还是有心,知道这词儿放这当儿不合适……只是眼下家里边还有些事情,都烦心着,若是让人听了去,总是不顺心的,戏易于温,这一阙过于凝重了……” 义明听闻也点头,亚兰所言,正是方才他开口想说的。旁边汉子忙点头称是,亚兰走至女孩身前,看看女孩儿手里,柔声问道:“这手帕……” 女孩儿哭着只说遗物,亚兰叹气,掏出手绢帮她把眼泪擦干,唤她说好妹妹莫再哭,以后在这当作自己家就好,劝慰一阵,女孩儿好歹收住哭泣,张姓汉子自是感激不尽。亚兰又跟着说些母亲生日排戏的事情不提。 道别时候,义明突然想起事儿来,开口问那女孩,说方才可是唱过《黛玉焚稿》,女孩儿诧异不定,摇头言说自己入行尚浅,还不曾学得这段,义明愕然,想是自己听错,也不再问,遂同亚兰出了院子。 亚兰告诉义明,说二姐那边妥了,本是来寻义明,听后院那孩子唱,跟过来瞧瞧,谁知义明已早到了,义明哈哈一笑,也把方才的如此一说,两人又都笑,加之大哥二姐的事总算又进了一步,不免松了口气,又谈了两句,各自回房不提。 § 人成各 今非昨 义明回房,洗漱停当,想这一日,竟似好几日一般。转头打开旁边带回的箱子,清点了些东西,思量了一番,复又关上。 上床躺下,脑子里竟昏沉沉,身子如坠雾中,听得方才那女子的声音,似在唱着《钗》中词曲。眼前是那手帕翻飞,霎时却又作了黛玉题帕的那块,心中好生惊疑,耳边呼呼风声,树枝嘎吱作响,那手帕变了长绫,忽又复原,耳边听闻有唱曰:“十七年苦生涯将我活怕,万种爱千种愁一齐放下”,便又是《黛玉焚稿》,已是剧末黛玉身死所唱。不免惊得一个激灵,却是一梦。 坐将起来,满头凉汗,稍定,想那林黛玉之自恨自怜自悲自欢,死前将宝玉所题之手帕、平素所作之诗稿,悉举投诸于火,其情其境,诚属可恨可怜可悲可叹。又想着世间女子,若牵情之一字,每思必多执拗。处富贵之境如是,处贫贱之境亦如是,根于天性,不可以人力为之变化。 思索良久,唯有叹息,辗转难眠,这般如此,直至大半夜,方才睡过去。 这一觉竟睡到大天亮,早些时候母亲差人来看,想他劳累,多睡睡也好,便没再叫他。直至此时,义明才被来人叫醒,听是国帮,声音尤为惊恐,忙问何事,答曰戏班子有人上吊死了,义明闻言脑子里一懵,片刻才回神,套了衣裳就跟国帮奔至前厅。路上闻言,果然是昨天那女孩儿寻了短见。 早有昨日那张姓汉子,坐地哭在那处,戏班子的人个个垂泪,母亲也是含泪气恼不语。亚兰红着眼睛,拉了义明一旁,告知事情经过,说今日一早戏班子的人起来便不见了女孩,四处寻了,大门的人说,女孩一早说吊嗓子出去了,最后果在后山寻见,一棵树上上了吊,已没气多时,只得收了回来,亚兰和母亲等人这才知道。 义明闻言不禁又惊又怒,问说昨日不已没事了么,亚兰转头看那汉子,汉子只管嘴里哎哟哭道:“昨日等小姐少爷走后,想着太太小姐少爷的好,心里感激,又因当时生怕惹恼了人,逐了出去,念及此处,后怕之余,一时气闷,说了些嫌她的话来,哪知她竟想不开,怪我,都怪我……” 母亲在旁听闻,问说昨日何事,亚兰转头简单说了,转头又问汉子说了什么,汉子闻听,好半天才说气恼之间,口不择言,说她莫要连累整个班子,现在外边处处兵荒马乱,出去如同寻死…… “我便说……你若要死,莫要连累他人,寻了你那爱人去……”一时间亚兰义明等人气得说不出话来,却有戏班子的人冲出来要打,旁边有人要拉,上上下下,乱作一团,好歹被母亲喝住,闹腾完毕,四下唯有凄凄呜咽之声。 亚兰定神,上前摇头忿道:“张大哥你这说的好个混帐话啊!她身世这样,你怎还下得了狠心,一时图个口快,就要了她的活命心思……” 张汉子呜咽言道昨日是那孩子爱人尾七之日,难怪她突然唱念起钗头凤来,实为纪念之意,自己一时忘记,说罢跪下去只管磕头,头捣蒜一般,哭的不成人形…… 母亲也是抹泪,旁边人劝慰莫坏了身子,好歹收住,言说那孩子虽不是本家人,却在自家了了性命,也是自家的事,该好好办其后事才是,又让汉子亲自料理着,也算赔罪,望孩子在天之灵可以饶恕,念叨其命苦,从此早登极乐世界便好了。再者这事情先不要让义明他们父亲晓得,免得又气恼,开先丈夫同意留得他们,只为自己生日将近随她高兴,搞不好这次听闻此事,要撵戏子们出去也未可知。汉子哭泣谢过,众人慢慢散去不提。留得亚兰义明两人,至最后仍是唏嘘不已,出了门,却见旁立着一人,仔细一看,竟是大哥义沛。 义明惊呼一声大哥,义沛却不搭理,眼里全没神采,手里一本什么书,木木卷了握着,嘴巴翻着不知念着什么。亚兰义明正要上前,他早转了身,踉踉跄跄急急走去,二人后面赶上,跟着义沛直接进了他房间,见他在桌前站定,任凭亚兰义明呼喊,只是不应。嘴里仍旧念叨不止,细细一听,只是一句。 我不如她。 我不如她。 我不如她。 我不如她。 亚兰急得跺脚,喊说这下可怎么是好,那边才去了一个,这边一个倒又生了心魔,事情紧急,顾不得许多,只好先去找母亲来。亚兰急去,义明留下来照顾着义沛,站定回首时候,眼见义沛只落得一个剪影,没在窗外打进来的一束一束日光里面,只幽幽的声音自光晕中传来,空空荡荡地在四周飘,时间恰似停驻,眼前灰蒙蒙,让人发晕。恍惚之中,听义沛稍稍停住,转头怔怔望着义明发愣,轻声唤他说:“……四弟……我不要……步那放翁……后尘……” 义明一时间,止不住热泪盈眶,上前拽住义沛手臂,哽咽难言:“……大哥……你……何苦来……” …… 母亲赶来,不免又是哭泣,心疼不已,义沛丢了魂儿似的,只管拉着母亲笑,说妈妈我想通了,想通了。母亲惊疑不定,又怕激了他,听他又说累了要睡,只管点头,亲自和义明等人安抚他睡下,待他睡熟,这才留下人看着,昼夜不离。 待到第三天义沛醒来,已复安定,亚兰义明连着母亲等人,也都找着空过来陪他说话,言谈间,也觉得确实是好了,众人都言,怕是当日那女孩儿的事情一激,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未可知。 § 钗头凤 那日夜里,义明领着国帮在义沛房间闲坐了一阵。告辞出来,到了廊子上,见有个小巧女子身影,趁着夜色钻出门去。国帮正欲上前,抬手指着,口里边只发出个“乌”音,胸口就由义明横手拦住,急停了脚步收了口,转头疑惑看着义明,见他只是不答话,略一思量,心中猜出几分,轻轻唤了声“少爷”,便回退了身子下去。义明仍望着愣愣立那儿,良久,才放下手来,长长地出了口气。 “……走吧……国帮……” “是……少爷……” 第二天,义沛不见了人。 事儿闹到义明那儿,义明只略怔了怔,也没惊慌。到了前厅,父亲正摔东西,母亲气得跺脚,连喝阿弥陀佛,叫说一个老的两个小的一个脾气,哪世作孽来哉。其余人惶恐不定,又是派人去找,又是劝慰太太,一家人正闹得掀天,突然间来了方家下人,说是他们家大小姐也没了人,方家老爷让来寻。 这一听事情多半有了定论,众人都惊得不行,二姐玉清跟雷劈似的僵住,母亲急火上头,一时间竟晕了过去,围上人去救过来,父亲左右顾不上,回身大骂方家狐狸精勾引他家长子,又扯什么军阀,什么道不同的事儿来,方家人听闻确是这边也有人没了,才慌忙回去禀报。此后多年,两家一直都在派人出去寻,总未曾寻到过;两家人一旦逢着,也是骂个不止,连着六妹碧清一个女孩子,稍大了点,竟也隔着田坎,和方家老七老八两个男孩子对骂,后来竟还追着打了,此乃后话,不提。 再说此时,义明帮着派人去找,又回头照顾好二姐母亲,闹腾好一会,直至午后才罢。出了二老房门,只觉恍惚,这些日子想来,如梦一场,不觉间到了大哥房间,却见亚兰已在里边。 亚兰只站着发愣,见义明进来,也不招呼,独独立在桌前,手里磨墨,好些时候,才幽幽说道:“……我方才照顾玉清睡下,也只拉我手不放,末了对我讲说‘三妹……看来只好断了’……” “她放弃了?”义明不禁一愣。 “还不作罢怎的,她倒是被大哥真真震了一场,只是妈妈都害了病,也不知轻重,现如今她可是家里年长的,再说她这性格,向来只管叫自己忍气,与他人方便……昨天那样子的闹腾一场,已是很出乎我的意料了……这从此看来,她再不会倔着,爸爸妈妈说什么都依了便罢……” 亚兰停了手,拍了两拍。 “方才妈妈睡下都还问我,义沛可有给我说么……我只得摇头……”亚兰耸肩言道,“大哥也是,爸爸妈妈不说,告知你我也好,这连去了哪儿都没讲一声……我道他这几日,真是好了,哪知早已有此打算。” 义明想想,说起那晚见义沛的事情来:“……告别时候,大哥叫住我,说‘四弟,父亲那可要你多帮忙照顾着了’。我想想,大哥既已不提婚事,父亲自然不会再恼他什么,宽慰他不必挂心,父亲开导开导便好的。他听闻只是笑,说父亲没那么容易消气的了。我觉他言谈之间,似有深意,只是末了,我仍只说‘大哥想哪儿去了,便有什么,做兄弟的也便给你顶着’。” 亚兰一听急道“你原已是猜出几分的”,义明点头,“……后来出去国帮还纳闷,说今日大少爷莫名地客气,告辞出来还要道谢了,我也只是笑,那时候,我看他已是下定决心……再后来……” “后来怎的?”亚兰话音未落,却往义明身后探头望去。 义明见状回首,见门口一小巧身影,便笑了笑,言道:“妹妹来的正巧……大哥他们,可是好好走了?” “好好走了……” “去了哪里,你可知道的?” “只管帮着约了时间地点,其余的,不曾来得及问……” “是么……想是也不知要到何处才能避得过……没个准儿……”义明言罢,遂从兜里掏出一对镯子,抚了两抚,惨惨笑了笑,“……带回来的一箱子东西,没来得及给你们,当中尚给他备着结婚时的礼行……这下不知,要到什么时候,才能送得出去了。”言罢复揣回兜里,沉沉叹了口气,抬头说,“……怕是难了……” 亚兰此时已回神过来,伤心不已,义明劝慰她,说“三姐,你道父亲真个为了一个八字恼的?错了,那会儿你没听到么……方家和我们,现在仰仗的,是不同的军阀,如何能结亲?若换作是你来,该要如何呢?” 亚兰又是发愣一阵,思索好些时候,才叹口气:“去了也好,只是连他怎么打的主意,都没留点蛛丝马迹可寻,真个把我等作了耍子……找来的时候,就这本东西……”义明见亚兰拾起桌上的一本书递过来,题曰《放翁诗集》,接过翻看,期间两页,被墨汁涂得漆黑。亚兰叹气,“寻思着这个可是线索不成?只是辨不出原本写的是什么……” 义明只是笑笑,没奈何递回去,摇头叹道“问世间,情为何物”,亚兰闻听问曰“四弟你已知道?”义明转头仍笑,良久,轻轻答了话。 “钗头凤……” 窗外茶花,已有一朵,正是开得绚烂时候。 |